首页圈子户外保险
一探归猿洞
作为一个外乡人,一直对清远本土的文化知之甚少。一次偶然的机会,在1993年版的《清远县文化志》里,发现清远的本土文化虽不算丰富但也并非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贫乏。看来,在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方面,我们需要补补课。如《峡山归猿记》,已经收进了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知道的人却不多。看了《归猿故事外话》后,勾起了我对考证归猿洞存在与否的无穷兴趣,心底也希望通过寻找归猿洞,将这一文化现象传承下去。
借助于本地网站的平台,我发起了一个有关峡江两岸文化资源的考证活动,并得到东方、布衣、夏至和大雄等网友的积极响应。清远电视台《北江纪实》栏目组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于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行人开始了三次寻找归猿洞的行程。
2008年11月8日,在飞霞景区管理处的康少云主任带领下,探寻归猿洞的活动拉开了序幕。这一次活动的目标,就是探寻九十年代前后开发的位于飞来寺后山西北的“灵猿神洞”。因1997年的山洪爆发冲毁了通往该洞的山路,该洞早已停止开放。
“十年没有上去了!”给我们带路的康主任感叹道。上面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也很想知道。
飞来寺的一些工作人员再三地告诫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通往归猿洞的路长期无人走,早已腐叶遍地,爬满青苔,而且山路毁坏严重,极为难走。据说2003年,上海某保险公司在后山拓展,一女队员不慎滑落悬崖摔死了。
此条路有多艰险?我们心中没数,正如对寻找归猿洞的路有多艰险一样一无所知。
在康主任的带领下,我们走到百步梯尽头,来到十九福地牌坊。然后,沿着牌坊后一条通往后山的小径,经飞来寺古寺原址(俗称大殿)、狮子石等景观一路上行。这一段路还算好走。山坡上尽是高大茂密的树木,几乎没有其他野草生长,路上腐叶不厚,虽有青苔,注意点就可以了。
至半山,始往西横行穿越。山路越来越难走,地上的腐叶也越来越厚,山洪肆虐过的痕迹随处可见。有的路完全被冲毁,需抓住树枝、野草小心试探、互相照应才能越过去。挡在路上的荆棘也越来越多,好在飞来寺的一名职工在前面开路,一路还算顺利。
终于,四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了所谓的归猿洞。洞在半山西北的一个悬崖上,洞口朝向西南,下方是仅2米宽的狭窄深渊。探头往下看,深不见底,深渊两壁长满野生植物。面向洞口,右侧山崖上有“灵猿神洞”大字,其中“猿”字与其他三个字的笔锋和神韵大相径庭,仿佛出自不同手迹,让人满腹狐疑。左侧的落款已爬满青苔,有点模糊,仔细辨认了很久,仿佛有“罗×”字样,奇怪的是没有年份。会不会是1884年重新修订孙绳祖《禺峡山志》的清远知县罗炜呢?如果真是罗炜,那么这个洞的发现至少一百多年了。
小心地踩着仅一脚之地的洞口边沿,攀住洞口两棵斜生的树干,腾空跨进洞内。整个洞呈口宽内窄,洞口边沿很不规则,高约2米,宽约1.5米,洞深2至3米,洞底高和宽只有1米左右。洞内光线幽暗,十分潮湿而且与洞外温差较大,摄像机镜头打开一会就蒙上了一层白雾。用头灯照洞,发现洞内有焚烧过的痕迹,只找到一根硬硬的箭猪毛。
蹲在洞口,仿佛蹲在光明与黑暗的边界。洞外阳光灿烂,秋风里树叶飒飒作响,洞内幽黑一片,潮湿如春天的夜晚。
几个人坐在悬崖边,拿着屈大钧的《二禺》篇,讨论此洞的真伪以及真洞的大体位置,讨论的结果竟是更加糊涂,屈大钧把我们搞得方位错乱了。如果《禺峡山志》中描述的“洞壑幽深”是指洞内,那么凭此可以证明此洞之伪,如果是指洞外这条深渊呢,则又可以证明此洞为真。问题是作者记述太简陋,而且文字的表达与理解往往需要很大的缘份。曾经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归猿洞历经山川变革和多次火焚后崩裂溃塌成今天这个样子?
回来后走访白庙村民,奇怪的是好几个宣称七、八十年代到过此洞的村民都反映此洞口没有题刻。如果他们指的洞就是这个“灵猿神洞”,那么,这个“灵猿神洞”的题刻时间应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这样看来,这个洞极有可能是为安抚慕名而来的游客而开发的一个伪洞。
当然,证明此洞为真,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着实有困难。而要证明此洞为伪,同样也缺乏充足的证据。或许,如大雄的朋友说的,从飞来寺西边三板桥谷口而上有两个幽深的洞,其中一洞也许是真洞?于是,大家开始期待二探归猿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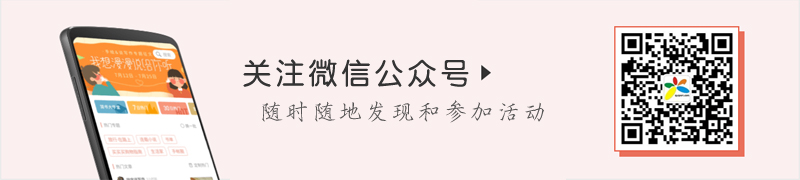
共8条回帖只看楼主
一探归猿洞的穿越路线挺不错! 集文化探秘 驴行健身于一体,难度适中,风景指数极高,可以开发作为清远运动休闲网的常规穿越路线.:victory:
相关链接:古纤道徒步 归猿洞探秘活动回顾http://www.qysport.net/bbs/viewt ... page%3D4&page=1
相关链接:古纤道徒步 归猿洞探秘活动回顾http://www.qysport.net/bbs/viewt ... page%3D4&page=1
粤ICP备14018191号© 2020 清远休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