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圈子户外保险
精神的守望者 —— <?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img][/img]2009年7月5日前往新桥疗养院探看老人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img][/img]
从新桥疗养院出来,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窗外,还是下着雨。刘伯那双凝望窗外的眼神,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华灯初上,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长时间。
今早与阳光家园的义工们一起前往新桥疗养院,探看24个患有麻风病的老人,这是我第一次前往此地。而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麻风病在过去,是不治之症,且误以为会传染,人们避而不及。直到后来经医学研究发现,麻风病不会传染。麻风病患者受到政府和爱心人士的关注,于是集资筹建了一间疗养院,接纳这些无家可归的患病老人。

汽车在停在疗养院门口,在接受完任务分工后,我从一楼走过,在走到17号病房的窗前,我的目光不经意与室内老人的目光重叠在一起,在定格的瞬间,我的双脚不由自主的走进这间病房。
老人姓刘,已是古稀之年。因12岁那年得麻风病,以至双腿严重残废,伸手更是不见五指。身材干瘪瘦弱,如同一副正被抽干水分的标本。老人习惯抽烟丝,一天总要抽上四五回。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地上全是烟丝的灰烬。可以想象,这间房已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来探望。当我劝说他少抽些烟,他不在意的往窗外探看。“唉。老了,心里有定数了”这让我想起古人的通天得道,知人达命。不经意的一句,老人对世事浮尘已惯,多多少少杂着无可言语的无奈。
打扫完卫生,我坐在他身旁。或许由于身体不便,他一直坐在床上的一角。被子似乎很长时间没有更换,经潮湿的天气,开始起毛。白色的棉花暴露在被单外面,成了灰黑色。整间屋子,隐隐有一种陈腐的气息,在空气中扩散,潮湿的,沉重的。
他与我坐得很近,我甚至能感受到他身体机能呈现缓慢的运作状态。他干瘪下去的眼睛,不时流出眼泪。他开始断断续续的说着往事。
在十二岁的那年,刘伯发现自己得了麻风病。在那个时代,麻风病不可治,人们极度恐慌的情绪被渲染得厉害。患有麻风病的人,家不过户,遭受亲人的遗弃和周遭歧视。刘伯父母相继去世,只留下年长刘伯两岁的大哥和大嫂。大哥对刘伯不闻不问,只有大嫂亲如母亲,对刘伯的生活起居无微不至。但后来,嫂子也因病去世。刘伯的生活失去照料,一度因病魔缠绕,陷入生死困境,生活苦不堪言。直到2004年,刘伯搬到新桥疗养院,才基本稳定了生活。
回首往事,刘伯眼里噙着泪光,我轻轻擦拭着,却无法抚平老人内心70多年来所经历的伤。
当我问道关于哥哥时,老人的目光又转向窗外,刘伯说,大哥今年已经80了,但有20多年没见过面了。只是在电话里,得知哥哥仍健在,有一个儿子,还住在老屋。。。。。。。
我问,你想回老屋看看么?
刘伯停顿了一下,“不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用了。”
我的内心,能分明感受到一个患有麻风病的老人,对故乡又亲近,又疏离的复杂情绪。“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人在暮岁,又怎能不想念自己的故乡,即使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毕竟对那片土地的归属感,是无法复制或转移的眷恋。而这种怀念亲人,想念大哥的情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无语话凄凉。
由于行动不便,刘伯的生活基本固于一室之中。一张木床,一张长方木桌,一部爱心人士捐赠的电视机,是构成活动的全部。刘伯经常坐在床上看电视,神经疼痛的时候,吃一包止痛散,饭菜定时有人送来,饭后总要抽支烟才舒服。日子就是这样坐在床上,看着电视不知不觉打发掉。刘伯喜欢看体育竞赛,说起比赛,年近八旬的老人神采飞扬,目光焕然有神。一台电视机,于我们而言不算什么,但对于刘伯,却是生命中最后的精神来源,满载着一个孤寡老人所有的悲欢和期待。或许只有在看电视的时候,在观赏一场场激烈比赛的时候,刘伯才能进行思想转移,在别人的竞技里,感受着生命的激情。那一刻,我相信刘伯所获得的精神满足,足以抵过千金来得宽慰。
可前阵子,电视机忽然出现故障,刘伯的生活忽然成了黑白状态。失去了激烈比赛的呐喊声,消失了精彩的画面。刘伯一时陷入无尽的空虚之中,无法安置孤独的灵魂。他经常坐在床上,抽着烟,凝望着窗外,一坐便是良久。没有人得知这个孤独老人在想些什么?也没有人可以理解老人无法捉获的空虚,寂寞和无助。这个姿势,无声胜有声,潜意识的反映出刘伯内心最真实的情感状态。这更应称为一种对内心渴求事物的“守望”,期待有一个人,期待给予安慰,哪怕是片言的寒暄。期待有人能得知电视机存在的必要性,期待有人会修好电视机。。。。。。
当我告诉他,我们会有人帮你修好电视机。他忽然转过头来,微微一笑,额上的皱纹深深浅浅,他问:“真的?”我斩钉截铁的说“是的”于是,我立马和一个女孩把电视机搬到云霄的车里,这时,云霄已接收了三台故障的电视机,并答应一定修好。那一刻,我想不仅仅是刘伯对电视机的存在精神依赖,其余的老人亦然。

刘伯对义工们一直充满感激。他甚至对我说,义工们还比亲人好。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这句话确实如是。那时候亲人恨不得抛下他,唾弃他,歧视他,而现在义工们接纳他,关心他,照顾他,让他倍感人间爱心所在。
他指着长方桌上的两朵用红色纸做的玫瑰花,仍记得两年前江门来的义工们给他折的。他一直用药罐把两朵花插着,如两年前她们离开时一样,还是那个位置。
他的目光,投到窗外。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停了。有鸟儿在树梢上叫了几声,天地忽然明朗起来。

临走前,我在一张纸上公整写上联系电话。刘伯接过,细细看了几遍,又平整叠好,拉开抽屉,放置最底的隐秘处。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情分,在于细微事物中的郑重。印证一句话,以诚感人者,人亦因诚而应。
我走出17号房,每走几步,总不自觉的回首。我的目光又与室内刘伯的目光重叠在一起,他坐在床边,看着我离去。他的目光是静止的,波澜不兴,停驻在12岁前那些发黄的记忆里。

从疗养院出来,我的内心进行一场独自清谈。这种情绪,无法与人交流,只能述以文,以思来者。
我忽然想到,为什么家园的人长期热衷于义工的公益事业当中,尽管辛苦,却甘之如饴。因为我们的内心,需要一场感动。如沈从文所言“城市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镜接触的声音光色过于疲劳,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之外,别的感觉器官有点麻木不仁。”朝九晚五的生活,尔虞我诈,趋炎附势,虚与委蛇,使我们的内心时刻处于浮躁的状态。更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生活本身的意义,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除了一次次满足欲望的所求,除了满足物质的占有,我们还有什么?

于是,在工作之余,参加家园的义工活动,给我们的内心注入强大的精神药剂,用来抵抗城市的现代精神价值观的侵入。在服务中,实现自我的存在价值。虽没有物质回报,但内心始终是丰盛的。

刘伯的目光,更多的是“守望”,是“期待”,期待被社会理解,守望一份人间最平凡的亲情。
而我们亦在“守望”,和“期待”,期待被社会的认同和肯定,守望一份恒定精神价值的回归。
 2009.7.5.晚上.
2009.7.5.晚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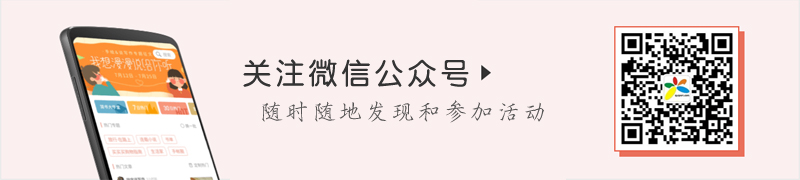
共11条回帖只看楼主
以前也参加过家园的活动,去孤儿院,不知道是我心理承受能力差还是我的爱心不足,看到孤儿院的小朋友很可怜,我自己努力哄他们玩,努力让他们感受童真,但是依然看到是迷惘的眼神,我就觉得,很恐惧这种凄凉的感觉,自己很无力,很心酸。后来,就只参加一些募捐之类的活动……
粤ICP备14018191号© 2020 清远休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