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圈子户外保险
二
远远看见对面山头的灯火阑珊,她像所有边缘事物那样,在黑夜的隐秘处兀自发光。仁青校长说,看呀。对面有灯火的地方,就是墨脱县城了。这让我们连日来,早已僵硬的屁股,得到些许宽慰。墨脱虽然说是通路了,但并不意味着通公路。道路基本是黄泥路,好不容易抢修完毕,随时一场雨,泥石流,塌方又会将所谓的道路给冲毁。连日作战的越野车,发出厚重的呼吸声。或许它亦知道终点就在前方,用尽最后一匹马力盘山行驶。
晚上九点半,我们抵达墨脱。我看到佛教《甘珠尔》藏经对墨脱的描述,遥远的东方有个“佛之净土白玛岗,隐秘胜地最殊胜”,是九世纪时红教始祖弘法数月选定的十六个莲花圣地之一和佛乐胜景, 100多年前,波密王就在此设宗(县),而这片富饶美丽的宁静之地,也是门巴族主要的聚居地。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墨脱原本不是门巴人的故乡,他们在近一两百年前,才从门隅一带东迁而至。传说东方有一块佛之净土,那里没有剥削和压迫,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那里风调雨顺,不种青稞有糌粑,江河之水为奶泉,不养牦牛有酥油。这对于生活在门隅一带受尽苦难和剥削的门巴人来说,太有诱惑力了。他们决定到东方去寻找这佛之净土。经历了与大自然风风雨雨的生死抗争,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白玛岗。虽然他们在这里没有找到幻想中的极乐世界,却在这富饶之地获得了自由,建起了村寨,并从此定居下来。在随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在门隅地区的门巴人不断东迁而至,繁衍生息。这就是门巴人东迁的传说故事。
我之前对于墨脱所有的想象,来自于朋友在06年徒步墨脱的经历。在他的描述里,墨脱是一个全国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城,这里由于地势险恶,人们进出只能靠双脚。只有5月到十月可以允许徒步进来或出去,其余时间皆是封山。然而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可以养活西藏一半以上的人口,但由于不通公路,石锅和筷子是运出大山的唯一商品。这里不通邮,东西只能寄进来,而不能直接寄出去。朋友对我说,在墨脱留下一个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盖到当地的邮戳。如今,他身在美国,每每想到此事,都为之叹惋。来墨脱之前,他叮嘱我,一定要给他寄一张墨脱的明信片。
如果不是亲自到达墨脱,我还以为它还停留在朋友的描述里。我充分享受到了国家十一五计划的有效成果,坐车进墨脱,可以寄明信片,而且最近,电信的3G网络也走进与世隔绝的墨脱县城。我的手提电脑在墨脱县城还办理了无线3G网络卡。通路后的墨脱篡改了我脑海里所有的想象。我们对墨脱的认识,始终是缓慢的。现代化迅速的进入这个封闭小城,它原本的面貌已经很难与现在的摸样重合。在行走中,这种想象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使我不断修正对墨脱的认知。我想到马丽华的一番话“我们本能的承认在场者的权威,这种权威来自于他们的身体,在一场电视转播的战争中,相对于演播室里夸夸其谈的专家,我们更相信战地记者。因为身在现场,我们相信身体胜过相信任何理念。”
天明,我从睡梦中起来。墨脱整个县城被雾气笼罩着,更显得其神秘性。在山坡上俯视脚下的墨脱县城,只有两条街道。道路很宽,两旁的钢筋水泥的平房屡见不鲜,很明显是最近几年才修建起来的。山坡上还有一排排整整齐齐的住宅区,全是清一色红房顶的水泥建筑。“住宅区”这样的名词随着随着墨脱通路后,在这个封闭之城找到落脚之地。老房子明显在劫难逃,无一不成为被凌迟的对象。现在很少人会住这些老房子。现在生活富裕了,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他们离开了老房子,在附近新建起了钢筋水泥的小矮平房。于是,街道里的新旧房子,成了传统与现代,旧与新对垒的楚河汉界,呈现出强大的对比。在精细与粗壮中,现代房屋无疑是这百年老房子的一大累赘。呆头呆脑的钢筋水泥,更像囚牢。缺乏老房子从容,幽深的诗意。在城市的发展中,现实利益总是试图消解着人们的审美精神,这样悖论让人哑然。祝勇气愤道“新的房屋穿插其间,就像蹩脚的后人,在画面的破旧部分,添补着败笔。”冯骥才分析说“器物与环境发生质变,在‘活着’的时候,他们是实用性的生活物品与生活环境。进入‘历史’之后,就变成纯精神的文化物品和人文环境。有些物件环境与器物由‘活着的状态’转变为‘历史状态’时,常被误认作无用的东西。旧时的房舍当作危房陋屋。”他更一针见血指出“这是由于人们用的是现实经济角度而不是用将来文化角度去看的。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已经“很难有一座城市,坚定的拒绝新世界流行的水泥和钢筋,坚持着它在传统中获得的栖居方式,美学风尚,和与此相依为命的日常生活。”②那些斑驳发亮的木房子。屋多半是木顶、竹顶或草顶的两三层小楼,以石块、木板或竹篱筑墙,屋顶为人字形,上层住人,下层关圈牲畜。夜晚在室内地板上铺粗毛毯或兽皮,和衣而卧。所有建筑门都朝东,因为他们认为太阳出来就照进家门,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木房子所有的细节都停留在最原始的状态,裹露着真实生活的本质内容。陈腐的气息,将几百年前的古老岁月,一一拉上帷幕。我看见光着脚丫的小孩,在老房子的木板上奔跑。仿佛置身于几百年前的荒蛮岁月里。美丽的门巴族妇女推开木窗子,探出头来,微微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我知道,墨脱县城里的呆头呆脑的水泥房子,不是我的目标。他们只是复制城市里千篇一律的囚牢,不具备探究的欲望。只有走进这样的老房子,我才能寻找到一条通往墨脱历史的线索。在一切的事物中,建筑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所有的历史痕迹,生活美学,思维方式,在这里以一种正在进行时状态,继续着他们依稀的梦。我多想走进这样的老房子,探个究竟。当我在门边轻轻的敲了一下门,却又将手缩回来。我怕惊扰一场睡熟的梦。
校长带我去墨脱中学参观,在此之前,我对它的全部想象,来自于一张张黑白图片。那些破旧的房屋,残旧的桌椅,赤脚上学的孩子,一张张渴望知识的脸庞。。。。。。这间学校在最近几年得到政府的热切关注,已经顺利完成了普九教育。图书室里的图书,有几千册,分类整齐的放在好几排书架上,基本上已经满足了学生的阅读需求。电脑室是最近一年才有的,三十多台电脑可以正常操作。电脑老师还说,现在电脑室还可以进行远程教学。学生宿舍和食堂在最近几年得到很大的改善,现在学校体育场正在修建跑道。如同墨脱中学的校长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想不到,墨脱通路使整个县城无论从城市的规划,还是教育上,有那么明显的进步。若不是地图清晰显示这里是墨脱,我真的以为自己到了内地某个县城。
网上很多驴友当得知墨脱已经通路,都纷纷表态没有去墨脱的必要。甚至他们对坐车进入墨脱的人,感到不屑。我不禁要问,难道我们就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忍心让同胞们继续忍受被长期封闭,与世隔绝的生活?难道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在网络上畅游四海,就不能让边缘的山区孩子享受到我们一样的待遇?难道我们可以享受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世界里,而让生活在墨脱里的人,继续过着刀耕火种,自供自给的原始生活?这样的冷眼旁观,窥测到人们内心深处的自私欲望。墨脱并不是作为旅游景点而存在的小城,它也有权利介于发展世界的大潮,也有权利分享主体社会让之全人类的一切文化财富。“当我们企图把一种文化,一种活生生的民族生活,从现代化进程中‘保护’起来时,我们是否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美感’?我们难道要通过这种方式将西藏在巨大的全球化体系中隔离在观赏的位置?那么,向往西藏的人,前往墨脱的游客,是否深藏着不可救药的空虚和自欺?”③
其实,我也在思考着墨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但无可否认,墨脱通路的确是门巴族人千百年来内心的热切愿望。有一些老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墨脱县城。他们一辈子守着一个封闭小城,须臾不离半步。从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也无从得知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一百多年来,背夫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以生命作为代价,走在一条艰险的古道上,汗水与尸体在大地上铺就了如今驴友的徒步路线。他们一只脚沟通外界的现代化工业文明,一只脚还挣扎在原始农耕社会的泥淖里。他们将现代文明驮在自己的肩上,承受着失去生命的风险,为黑暗,原始的墨脱带来了一束希望之光。
而现代人无法理解背夫的艰难,无法理解门巴族人对外界的向往,更无法理解一个民族的百年来的苦难,也就无从给予慈悲。他们等了一百年,盼了一百年,修了无数个日与夜。从1953年开始,便一直在修墨脱公路,可每次大塌方,泥石流的冲击,瞬间冲毁了所有的道路,桥梁。当你看到抢修多日道路,又被一场夜雨给冲垮得面目全非,你无法不放声大哭。有一种希望,在一百年前就开始埋下了种子,生根,发芽,得到过阳光的滋润,又惨遭几次枯萎。为了这条路,死的人不计其数,门巴族人生存的绝望和希望都寄托在这条百年来奋斗的道路上。
现在,墨脱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了现代人谈资的时尚名词。当游客为自己徒步墨脱,露出一脸得意的表情时,真正的墨脱已经离他远去。他们的目的更多的出于一种“征服”而不是“理解”。除了掠取几张照片,证明到此一游,用以满足内心深处的虚荣心,和填补他们内心的无法排解的空虚,他们一无所获。事实上,墨脱的美感,只是为了取悦自身,无意获得众人的嘉奖。莲花的圣地,始终是在远方。不仅仅是道路之远,还是精神寻索的之远。于是,我对游客,一直持着怀疑的态度。
离开墨脱,身旁的人不理解,我的内心既愉悦,又矛盾重重。一方面,墨脱的通路宣告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希望墨脱在通路后,早日脱贫致富。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墨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精神上继续做着千年前的梦。在传统与现代,在更新与保留,在物质与精神中,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的中轴线,以不至于向任何一边倾斜。这将是墨脱长期要面临的问题。
备注:①《西藏当代旅行记》中闫振中《总序》
②《幸存之城》见《于坚集》卷四,13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李敬泽《山上宁静的积雪
多么让我神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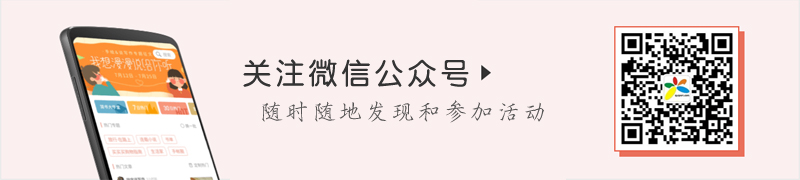
共3条回帖只看楼主
粤ICP备14018191号© 2020 清远休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