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圈子户外保险
关于一个梦想,和荒蛮岁月
想在墨脱支教,出于三年前的愿望,没想到这个心愿如今实现。经校长仁青罗布的同意,和墨脱县教育局的批准,我在背崩小学支教一个月,担任音乐老师。我走进这间小学,大门左右有两块竖立的木板,用藏文和汉文分别写着“墨脱县背崩乡上海印钞厂希望小学”和“背崩乡完全小学”牌子的背后,隐藏着一条历史线索。校长仁青罗布开始给我讲述这间学校的历史:这间学校建于1976年,当时在校学生只有25人,只有仁青罗布一个老师。宿舍和教学楼各一间,还是竹木结构的。到1979年,学生有30人,竹木结构的房子换成了木板房,多了一个老师——桑阿曲杰(现已是墨脱县教育局长)。1987年,开始修筑石头结构的教师,和宿舍四间。学生增至70人,老师有四人,分别开展了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教学。直到1998年,上海印钞厂的离休老人陈真,已到古稀之年。却不畏艰难险阻,千里迢迢,翻越四千多米的多雄拉雪山,来到背崩乡小学实地考察。最后,在这里全国唯一一个未通公路的墨脱县创立第一个希望小学——“背崩乡上海印钞厂希望小学”
捐助60万元人民币,修筑教师,学生宿舍,伙房。当时学生132人,老师9人,开设了一到五年级的教学。到现在为止,已经修筑了食堂,和学校围墙。学生接近350人,老师增至有二十多个,可以开展一到六年级的正常教学。。。。。。。。
当我在陈述这些历史时,脑海中浮出一些影像。仁青老师站在三尺讲台,台下三十双目不转睛的眼睛。陈真老人的身影,黄鹤白发,蹒跚的翻越多雄拉雪山。学生挨个在的传递砖头,脸上全是水泥灰,笑的时候,露出干净洁白的牙齿。校长说,学校门前的那条小路,是老师和学生亲手修筑的。我已经看不见修筑时,留下的汗与泪。我只听见不远处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完成一个三十多年的梦想。我想象着,在不通路的情况下,一砖一瓦完全是靠背夫背进来,他们要来回多少次这“令人听此凋朱颜”的生死之路,他们被蚂蝗咬过多少口,要翻越多少次雪山,要经历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背夫永远埋在雪山下。我也不清楚,每一块砖下,饱含多少汗水和血泪。在这条道上,我感受到人的渺小,而自然的法力无边。这间学校不断的改变,我看到时间发出断裂的声响。有一根白发,从仁青校长的额头上悄然萌芽。
仁青校长,为这间学校付出了人生最宝贵的三十年。从25个学生,到现在300多人。从一个老师,到现在20多个教师职工。他的肩膀上,扛着三百多人的梦想。这一路走来,他不断披荆斩棘。其中的辛劳,难以一言而尽。2005年背崩乡遭遇暴雨,泥石流,他亲自到地东村(背崩乡里其中一个村)组织自救。返回学校后,顾不上喝一口水,马上召开紧急回忆,为无家可归的村民,和孩子捐粮捐物;教职工的伙房长年失修,遇上刮风下雨,就成了“水帘洞”,校长无偿的捐出自己准备新建伙房的备料;为了学校的发展,他经常东跑西要,上下奔波,为学校筹集资金购置学生的铁架床。让孩子们告别了睡地铺的历史;当得知考内地班要考计算机知识,他又一次犯愁,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考试不“吃亏”,他找单位,跑部门,要来五台电脑,连夜请来民工,千叮万嘱,要把“宝贝”运进学校;每年,他不顾年迈体衰,坚持翻越巍峨的多雄拉雪山,到林芝地区亲自督办教材,资料,主副食的背运。。。。。。。
这间学校,成如容易却艰辛。而其中的艰辛,鱼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从一排教师宿舍走过,全是以石头做外墙,里面是木板。那被时光打磨得发亮的木门,上面吊着一串白色的鸡蛋壳,在阳光下特别耀眼。木板的灰暗,与阳光的强烈对照,鸡蛋壳闪闪发光,构成一副极具美感的图画。副校长和老师特别热情,给我空出一间房子。房子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他们又为我张罗铁床,被子,枕头。得知我在写作,还给我搬来长方桌子。晚上,校长和教导主任还招呼我吃饭,满桌的好菜。虽然都是城市显得很不起眼的菜式,但在这里,可以算得上是饕餮盛宴了。房间里没有电插板。第二天,懂得电工的老师给的房间安装好一个四孔的电插板。这里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物价很高。一桌一椅,来之不易。他们的安排,让我感到人情的温暖,如三月春花。
学校现在还没有洗澡房,这里的孩子都是到河里去洗澡。对于女老师来说,洗澡的确是一件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里的九月份天气还是很热,午后往往汗流浃背。前几天还能擦擦身算了。最后,终于忍不住满身的臭汗。我知道身体已经发动了最后的警讯,强烈要求洗澡了。在一个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了,周围没有灯,黑漆漆的。我与一个女老师,静悄悄的跑到全校唯一一个水池的地方。一人把风,一人洗澡。冷水很凉,水直接往身上冲,有一种快感迅速的进入身体每一根的毛细血管,不由得让我轻轻的尖叫了一声。怎一个冷字了得!这样的洗澡,总是有种不安。害怕此时若有人走过,看见一丝不挂洗澡的老师,未免成了墨脱地区一桩“艳照门”。匆匆洗完后,就急急忙忙的跑回宿舍。这样的洗澡,可谓是大胆。后来,这样的洗澡方式,已经成习惯,就不再害怕,一个人也敢去洗了。现在听说学校准备修建洗澡房,有热水供应。于这里的老师和孩子来说,实在是期盼已久的事。
这里的老师,都是自己做饭。几天下来,我的确很好奇,这里既没有市场,也没见过卖菜的贩子,菜是哪来的呢?后来才知道,原来隔一段时间,便会有村民背黄瓜,青椒等蔬菜到教师伙房来卖。老师们往往一买,便是好几天的。村子里若要杀猪,杀牛,也会来学校提前通知一声,然后预定好要几斤肉,按照预定的时间,一大早就要到村民家去买。若去迟了,也许就要空手回来了。所以,在这里的商店,你总能看到一些肉类罐头。猪肉的,牛肉的。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一下伙食。这里的物价很高,通常是内地的3到5倍。最奢侈的一件事,便是在大汗淋漓的时候,到商店买一瓶10块钱的冰冻可乐。这里无论是矿泉水,还是可乐,雪碧,都是十块钱。而且都是一口价,谢绝还价。这里的鸡更是要150元一只,让人不得不感慨内地的物价水平真是低呀。物价昂贵也倒算了,有钱也未必卖得到东西。我为了一张充值卡,跑遍整个村子的每一家商店,寻寻觅觅,最终还是失望而归。被迫停机,最后还是通过朋友在网上给我充值,才恢复了正常通讯。
在背崩支教,住简陋的房子,吃清淡的菜肴,身体遵循着一种减法原则,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想到书中周国平所说“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目的就是为了不当物质欲望的奴隶,保持精神上的自由。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得好:"自由人以茅屋为居室,奴隶才在大理石和黄金下栖身。"柏拉图也说:胸中有黄金的人是不需要住在黄金屋顶下面的。或者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非常喜欢关于苏格拉底的一个传说,这位被尊称为 "师中之师"的哲人在雅典市场上闲逛,看了那些琳琅满目的货摊后惊叹:"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呵!"的确,一个热爱精神事物的人必定是淡然于物质的奢华的,而一个人如果安于简朴的生活,他即使不是哲学家,也相去不远了。”我当然成为不了像周国平那样哲学家,但我恍如走进了荒蛮岁月,褪去长居城市的外衣,融入当地生活。每天教书,洗衣。阅读,写作。在山中待久了,觉得自己俨然成了一个村姑,粗布麻衣,呼吸晨昏,俯仰天地。内心丰富安静,精神丰盛自足。身体与泥土皆是洁净的,雅鲁藏布江在我怀里安妥睡着,发出轻微的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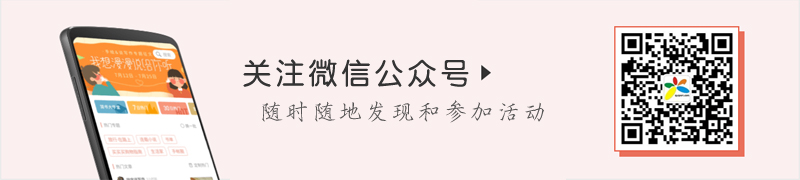
共2条回帖只看楼主
粤ICP备14018191号© 2020 清远休闲网